
又一家豫章書院 這里的孩子每天做噩夢想自殺(圖)
原標題:扇巴掌、踢肚子、用鞋刷抽臉,又一家“豫章書院”!這里的孩子每天做噩夢,想自殺
還記得
山東臨沂網絡成癮戒治中心
用“電擊療法”戒“網癮”嗎?
還記得
江西豫章書院
以“鞭子抽、關小黑屋”懲罰學生嗎?
這些打著“戒網癮”等旗號的特訓機構
頻頻引發輿論口誅筆伐
但即便如此
虐待兒童的痛心事還是一再上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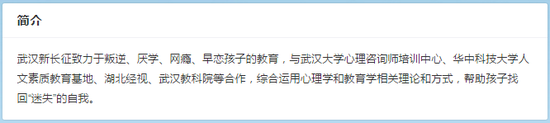 微博認證:武漢市洪山區新長征心理咨詢中心
微博認證:武漢市洪山區新長征心理咨詢中心今年3月31日,記者走訪新長征,看到校區正在裝修擴建,錦繡山莊門口曾懸掛的新長征牌子消失了,學校樓前的牌子仍在。一位閔姓老師告訴記者,目前暫停招生,預計5月底恢復。另一位在山莊工作的人士透露,學員在春節前都已被家長接走。
經記者多方確認,新長征已被一家叫湖北紅心教育青少年成長特訓營的機構收購,其創始人付德寶對此予以肯定。紅心基地特訓營主任袁曉峰告訴記者,他們主要是以“行為訓練和體驗式心理培訓”解決青少年網癮、厭學、叛逆、早戀等問題,在湖北省有8個基地,其中在武漢有3個,一直在開班。
這所位于武漢市江夏區五里界錦繡山莊內的青少年成長學校,自2009年來,接納的學員最小10歲左右、最大的28歲。多名受訪學員告知:與體罰同時存在的是思想控制,告密、舉報之風盛行。

在武漢新長征藝術培訓學校
有人曾經絕食抗議
有人曾經喝洗衣液“自殺”
還有人從二樓樓梯的欄桿上翻滾下去
。。。。。。
“問題少年”并不新鮮
針對“問題少年”的機構屢見不鮮
但鮮少有人真正傾聽少年們的心聲
在青春叛逆的那幾年
被扔進一個充斥惡意的陌生世界
他們究竟經歷了怎樣可怕的事?
進入新長征:深深的受騙感
少年們因為五花八門的“問題”被送進新長征。有的是厭學逃學,有的是早戀,有的純粹就是“跟父母沒話說”。讓我們來看看這些把孩子送進新長征的奇葩理由:
網癮
文清是在2016年7月2日被父母假借“看病”為由帶到新長征的。剛進去,她便被教官從家長身邊帶走,“散散心”,其實就是在山莊里瞎轉悠,回去時已不見父母蹤影。而剛剛還笑臉盈盈的教官馬上“變臉”:“你得待在這里,待多久看你的表現。”
至今文清也想不明白,父母為何要送她到新長征,自己不過是“喜歡和朋友出去玩,有時通宵上網而已”。出去后,文清當面質問原因,得到的答復是:“你要是聽話我們會送你進去嗎?”
大部分男生都是因為網癮進來的。有個10歲男孩進來的時候口袋里裝滿游戲卡,天真地去找老師借手機打游戲。
跟父母吵架后去朋友家睡了一晚
韓笑雪2013年6月被送進來。據她告知,上初一時,有天她跟父母吵架后賭氣去朋友家睡了一晚,家長以“轉學”為由開車將她從孝感帶到新長征。
2014年9月,從新長征出去半年多的韓笑雪,是被山東科技防衛專修學院的教官直接開車到她家、從她房間帶走的,“從早上6點開到了晚上7點才到學校”。
韓笑雪剛記事起父母就離婚了,她跟著外婆長大,后來在父親組建的新家庭住了幾年,“沒有一天像家的感覺”,又搬回去跟外婆住。正是在這期間,她接觸了一些不好的人,開始“變壞”。
在電視上看到新長征的節目
來自鄂州的劉珺則是父母在電視上看到新長征的節目,覺得“在里面聽聽道理、做做游戲挺好,就當體驗生活”。
懷疑孩子喜歡同性
有個女孩是因為父母懷疑她喜歡同性,被送了進來。
學會抽煙、迷上跳舞機
學會抽煙和迷上跳舞機后,趙小帥和父母的關系日趨緊張,有天早上他被母親叫醒,看見母親一直對著他笑,“眼里含淚的那種”,感到莫名其妙,接著他便被父母以到山莊游玩為由帶到了新長征。
離家出走
離家出走一個星期的藍琪,被母親“以后再也不會那樣”的承諾騙回家,一覺醒來,新長征的教官出現在她家里。
 新長征實行軍事化管理,女生宿舍的被子必須疊成“豆腐塊”。
新長征實行軍事化管理,女生宿舍的被子必須疊成“豆腐塊”。回想起進入新長征的過程
每位受訪學員都有一種深深的受欺騙感
TA們說:
明白自己落入騙局的一剎那
“差不多就要崩潰了”
“對生活毫無希望”
有人抱著床桿哭了一整夜
有人被“一走進去就能感受到的壓抑氛圍”
嚇得不敢吭聲
還有人則在很短時間內明白了
這套父母與校方之間“成年人的規則”
開始裝乖賣巧、討好教官
目的是為了早日出去
一人犯錯,全體受罰
新來者首先須上交全部個人物品,包括身上掛著的“傳家寶”,接著換上新長征校服。當時文清被帶到一間教室,“已經被一股受騙的氣沖昏了頭腦”,她拒絕換校服,大發脾氣。教官過來抓她的頭發,她拿起一塊木板回擊,打在教官的頭部,“因為從來沒有人這樣對過我”。教官二話沒說,一把扯住她頭發,拽倒在地,指揮旁邊幾個女生將她的衣服撕掉,強行換上校服。
接下來3天,文清沒有吃飯,喝了半瓶花露水,心想肯定會被送去醫院洗胃,但結果沒有,隨之而來的是懲罰。教官把她帶到3號樓2樓的活動室,拎來一桶純凈水擺在面前,叫一名學員把水倒進漱口杯,讓文清當著所有女生的面,一杯接一杯把水喝光。
陳靜是記者找到的在新長征時間最長的學員。她今年18歲,從2013年5月第一次進去,到2017年1月出來,先后3次,一共3年零5個月。
一個星期后剪頭發,陳靜進校時的黃頭發、一邊長一邊短的劉海,都沒了,變成“前面到眉毛、兩側到耳朵”的標準發型。有個女生,頭發從3歲養到11歲,長到膝蓋了,“咔嚓”被剪,當場就哭了。還有的女生半年不來月經都不能被送進醫院。
在陳靜這位老生眼里,新生文清的所作所為“很傻”。老生們早就見慣了。新人初來乍到,通常都要先鬧幾天,逃跑、絕食、喝花露水或洗發水、啃肥皂,一律受罰。
趙小帥來的第一天就沒吃晚飯,當晚連拉3次緊急集合——都是深夜12點以后,哨子響起1分鐘內所有人必須在大廳站好隊。趙小帥被綁在床上,第3次集合才參加。教官讓他把之前的深蹲都補上,一共300個。
在新長征,多數學員待半年左右,不斷新老交替。學員們告訴記者:躁動期只在前3個月,后面會越待越老實,因為開始數著日子期盼出去。那些“不聽話”的新生被視作害群之馬,他們做錯事所有人都會被牽連,“一人犯錯,全體受罰”。
新生之間溝通是大忌,老師、教官和老生都會隨時盯著他們。一般過3個月后,新生被當作老生看待;也有“冥頑不靈”者,半年多了還是“新生”。
扇巴掌、踢肚子、用鞋刷抽臉、被灌一整桶水。。。。。。
韓笑雪至今難忘,山東科技防衛專修學院電擊的慘叫聲。那個女孩是“三進宮”,被送來時又哭又鬧,“教官說‘你再喊一句’,那女生就喊了一聲,教官抄起電棒就電她”。
新長征沒有電擊,但韓笑雪覺得新長征比山東那所學校更壓抑,“不給尊嚴和人格”。2013年,她親眼看見一個女孩被教官勒令把雙手放進糞桶里,泡了近1分鐘,只因為女孩在澆糞時露出“嫌棄”的表情。
在陰暗的走廊里,學員們常常見到一位20多歲的男學員,雙手被捆綁,跪著一動不動。
在受訪學員看來,體罰毫無來由。每位教官都有獨特的懲罰方式:蔡英哲喜歡拳打腳踢;丁海濤喜歡扇巴掌;韓瓊喜歡拿木凳往男生身上砸,對女生則踢肚子。那個被勒令把手放進糞桶的女孩,被同一位教官用鞋底打臉。
有人站著時冷不丁被教官絆到地上拳打腳踢,有人冬天被潑十幾桶冷水,也有男生被幾個人壓在墻角劈叉。跑圈、沖刺、蛙跳更是司空見慣。一位學員慨嘆:“最舒服的懲罰是在床上被綁成一個‘大’字三天三夜”。
 那個逃跑三次、被打得最慘的女生,就是被吊在這棵樹上灌水。
那個逃跑三次、被打得最慘的女生,就是被吊在這棵樹上灌水。所有人都知道那個逃跑3次均未遂的女孩,因為她被罰得最慘。
她被要求圍著操場跑200圈,跑不動了,教官過來用鞋刷抽她的臉。正在一旁刷鞋的女生記得,“最起碼抽了三四十下”,鼻血用完一包紙也止不住。
接著是對待逃跑者的常規項目:灌水。她一只手被吊在樹上,有人用漱口杯給她倒水,一杯接一杯,直到喝光一桶18.9升的純凈水。女孩被放下來后,躺在地上發抖——這是2014年3月,女生們坐在一旁的臺階上看著,男生在打籃球,偶爾有人瞥一眼。
唯一逃跑成功的那個女孩成了新長征的傳奇。她是“五進宮”,對新長征了如指掌。有次她單獨在2號樓打掃衛生,趁女老師洗澡時跑了。那是下雨天,她里面穿著便裝,一邊向山莊門口跑,一邊脫校服,跑出去躲到附近一戶人家,最后是朋友來接她離開。女孩生于1997年,逃跑是在2013年。
那晚,所有學員集體受罰。陳靜回憶說,教官讓他們坐到凌晨3點不準睡覺。從那以后,管制更嚴了。
逃跑在新長征時常上演,要么在2號樓和3號樓的鐵門縫隙里,要么在洗衣液、花露水的泡沫中。實際上,它幾乎每晚都出現在學員們的夢里。
有人想在跑步時從圍墻邊踩著樹翻出去;有人想上文化課的時候借口說肚子疼上廁所跑出去;還有人趁罕有的外出機會勘測地形,發現“有部分欄桿很矮,外面是田野”,翻出去后能跑多遠跑多遠,看到車就攔車。但他們都不敢。
在新長征,逃跑失敗帶來的是最嚴厲的懲罰,而且必須所有人都在場,“就像看戲一樣”。韓笑雪曾參與一次逃跑計劃。6名女生把上鋪支撐床板的鐵抽出來,去撬女生校區的鐵門,一天撬一點,撬了兩夜,第三天不敢撬了,第四天就有人舉報。
逃跑失敗,幾個人趴在大廳被教官用棍子打。當晚居然拉了55遍緊急集合,隔6分鐘拉一次,從晚上11點多拉到次日早上約5點。每次教官還進屋檢查,鞋子沒擺好打一棍,蚊帳沒弄好也打一棍。
接著是關禁閉。韓笑雪被關一周,最長的關了20多天,因為在禁閉室喝洗發水自殺。每次逃跑事件發生之后,伴隨而來的是管制升級:策劃逃跑的女生被從2號樓轉移到更封閉的3號樓;晚上老師用柜子把門擋住,每人發一個盆,上廁所就用盆解決。
韓笑雪曾獨自躲在廁所喝下半瓶花露水,但只是難受了一會兒,“和別人說就是自找苦吃”。
 六個女生策劃撬門逃跑,右邊那扇木門外面還有兩道鐵門。
六個女生策劃撬門逃跑,右邊那扇木門外面還有兩道鐵門。1999年生的趙小帥把食指的長指甲咬成錐形,劃傷手腕,又將一塊鐵皮磨得鋒利,在手臂割了140多刀,腿上還留下一個“井”字疤痕。后來,被綁在床上動彈不得,傷口簡單用衛生紙清理了事。
女生們談起這個自稱會武功的男生都笑了——練過兩年武術的他跑去跟教官單挑,被兩名教官打趴在地,躺了兩個月。
比割傷、流血更讓趙小帥感到痛不欲生的卻是數米——教官把黑米、白米放在一個臉盆里,攪拌,勒令趙小帥把它們分開,并數清楚黑米、白米有多少顆。晚上10點熄燈后,趙小帥蹲在走廊揀米,通宵數,持續了整整一周。
那段時間,晚上不能睡覺,白天罰練體能,趙小帥接近崩潰,“我們再做錯什么事,也絕對不應該被送到這種地方來啊!”
還有一種無聲的反抗。
學員每周六申請添置日常用品。有個女生每次都買幾大卷衛生紙和許多生活用品,用不完就堆在宿舍,“把新長征的倉庫買空了,把爸爸買窮了,就可以回家了”。
在新長征,兩位學員之間關系好的最高境界就是分享零食,因為零食太寶貴。不過,為了控制學員,老師和教官們會刻意挑撥學員關系。如若兩位學員較為親近,則會被勒令跑步,一個人跑,另一個人在后面踩前者的腳后跟。
“當其他人都在訓練,你被老師叫出去辦事,那個感覺很爽。”陳靜說,除了物質,獎勵也有精神層面的。
而互相舉報,最易獲得獎勵。
從新長征出來后,每天做噩夢,想自殺
離開新長征的第一夜,趙小帥記起之前被學校收繳的書包里還有20元,他想也不想就去買了一包煙抽。
“其實就是強行控制出一個乖孩子。”陳靜說。在新長征長達3年多的她,現在不再控訴對學校的不滿,而是把憤怒矛頭直指家長,“基本與爸爸隔絕了,老死不相往來”。
“剛出來的時候細聲細氣跟爸媽說話,不敢反抗,后來是壓抑不住的憤怒,跟我爸拳打腳踢,用臟話罵他。”趙小帥說,從新長征出來第一周,他被檢查出患有中度抑郁癥、輕度焦慮伴隨狂躁癥,每天做噩夢,想自殺,“我爸媽常常半夜來我房間試探我還有沒有呼吸”。
大多數學員一離開新長征就“翻臉”。藍琪剛出來后曾向父母如實介紹,得到的回應是“別人都很好,就你特殊”。
3月25日,記者在武漢一家咖啡館見到韓笑雪。她戴著帽子,鴨舌壓得很低。一起出現的是比她晚幾個月進去的藍琪。二人在新長征結識,當年都是13歲,都曾為長發被剪而痛惜。
聊起新長征,她們看起來很輕松。韓笑雪說起她有兩次沒聽到哨子聲而害得所有人被罰時,哈哈大笑。藍琪說,現在已離開幾年,心態不一樣了,如果是剛出來時,會說得越嚴重越好,“滿滿的怨氣,跟反社會那樣”。
3月31日,趙小帥和陳靜帶著記者重回新長征。已離開近1年的趙小帥,仍擔心再見新長征“會讓自己受不了”,特意找了一位男同學陪同。
新長征所在的江夏區五里界鎮錦繡山莊,是占地600多畝的度假休閑區,離市區近40公里。放到武漢市地圖上來看,相當于“郊區的郊區”。那天,有大人小孩在玩戶外游戲,一群大學生在燒烤露營。
趙小帥和陳靜對這里的一切記憶猶新:哨響拉開一天序幕,6點起床,跑操、洗漱、整理內務,上午是隊列,下午是體能訓練,僅有不到10%的學員在家長堅持下上文化課,晚飯后所有人在活動室寫日記,晚上10點熄燈。
所謂的心理治療是“面子功夫”。在新長征官網上的教授講座、文藝活動,好幾個月才有一次,“學校趁這個機會瘋狂拍照”。一位來開講座的老師對學員說“你們快要放寒假了”,韓笑雪使勁憋著,不敢笑出聲——新長征還有寒假?連春節都是在這里過。
新長征的學費是半年3萬元。學員們不能出去購物,只能向老師申請。“比外面賣的貴很多倍”,陳靜說,最離譜的是有位學員曾用50元買了一個梨。
新長征規定進去兩個半月后才能見家長。藍琪趁教官不在,偷偷對母親說:“這里每天都打人,趕緊把我接出去。”母親不信:“看你平時照片挺開心的。”家長們不知道,照片是精心挑選的“開心時刻”,信是經過老師審核之后才寄出的。
在外界看來,被送進新長征的孩子是莫名其妙消失的。那個被罰得最慘的女孩跟趙小帥家離得很近,“初中她就不見了,不知道她去了哪”。直到2017年,趙小帥被學校叫去撕學員檔案,他突然看到那個女孩的名字,再看家庭地址,確認無疑。檔案上寫著女孩的父親認為她有“自殺、自殘行為和心理疾病”。趙小帥出來后特地去找了那個女孩,女孩對其父親說辭矢口否認,她已在認真備戰高考。
離開新長征后繼續學業的并不多。韓笑雪自初一起,先后被送進“特訓”機構兩次,“再也沒有完整上過學”。
受訪學員都說,他們不曾見過一個人因為進入新長征而變成“好孩子”。很多人會變本加厲地玩,少數人的改變則是隨著年齡增長自然而然地對那些玩法失去了興趣。
少年們與父母意志的反抗依然在繼續,只是用了更含蓄的方式:趙小帥為了抵制當兵,偷偷在左手臂刺青;文清一人從家跑到武漢工作;藍琪正在申請一所美國高校。
當然,也有父母對孩子表達過歉意。他們后悔在不了解新長征實際情況之下就把孩子送進去。
藍琪覺得與5年前把她送進新長征時相比,父母的“意識形態”并沒有變化,“始終覺得我達不到他們的期望”。現在母親很少跟她講話,父親總是“上帝視角”地教育她,講一些空泛道理,“沒有沖突,也沒有理解”。
趙小帥如今看起來很瘦。在新長征的半年里,他的體重曾經從96斤飆升至134斤,“每個人都會變胖、變黑”。
文清還記得她第二次從新長征出來,去朋友家玩,朋友竟沒有認出她。當她自報名字時,朋友哭了,“你怎么變成這樣了?”
比起身體的折磨,寫小紙條更讓學員們感到恐怖:“動不動就讓我們搬個小板凳,寫最近聽到的看到的所有”;“純粹為了制造詭異和壓抑的氣氛”。
3月31日下午2點,太陽照在新長征的操場上。 “再有5分鐘該起床訓練了。”趙小帥對著空蕩蕩的操場自言自語。
3號樓前挺立著一棵樹。他突然駐足說,這叫“過年樹”,過年時樹上的葉子全部掉光,開春了才長嫩葉。
對這些少年而言,新長征就像青春記憶里的一道疤痕,只能等待自愈。
當年離開新長征,藍琪偷偷將一位好友寫給她的一封信夾在內衣里帶了出來。那位好友曾在她受罰時抱過她一下。信里的話,藍琪至今還記得:“如果說世界是太陽照得到那一面,新長征就是太陽照不到的那一面。現在,你自由了,忘了這里,去看美麗的風景。”
孩子變得聽話就叫“矯正成功”?
“看了你轉發關于新長征學校的文章,心情很沉重,爸媽當年的方式也許不對,但那時的我們真的沒有更好的辦法……希望你好好聽話,不要再想之前的事,人生還很長,爸媽只有你一個女兒,我們真的非常愛你。”
4月7日晚,文清的父親發給她一條長長的消息。
這是極少的愿意正面回應的家長。
回訪時記者了解到,家長們態度不一,有的只是簡單對孩子說“希望你放下過去”,有的索性不愿提及。
事實上,在明知這所特訓學校存在體罰和人格侮辱行為的前提下,許多家長仍舊堅持把孩子送進去。因此,不少學員都至少是“二進宮”。
在自我意識正在形成、發展的青春期,打著“青少年行為矯正”旗號的特訓學校讓這些所謂的“問題少年”提早見到了世界的殘酷一面。
有網友說,楊永信就一個人,而臨沂網絡成癮戒治中心的學員那么多,為什么任其電擊卻不反抗?
同樣,在新長征,教官和老師加起來最多十來位,過年時只有兩位老師,但依然無人敢反抗。

我的受訪者都告訴我,真正的可怕并非電擊和體罰,而是維持其“統治”的那套秩序。
人群聚集的地方總會有規則和秩序。新長征有一種特殊到詭異的“層次感”:學員被分為新生和老生,老生中有那么一兩位是“受寵者”,享受跟老師“出公差”的待遇;流動頗為頻繁的老師和教官們,由一位中年婦女管理,而這位婦女年僅5歲左右的兒子,只要每次出現在學校,老師們都會陪他吃飯、喂他零食,這位婦女還會讓小男孩到女生學員中挑兩個陪他玩耍……
我的同事采訪過楊永信的臨沂網絡成癮戒治中心,當時他被一群家長團團圍住,被要求刪除照片。同事不可置信地問家長們:孩子就這么不可救藥,一定要送來這里?一位父親反反復復地嘆氣,能做的、能想到的,我們都嘗試了。那些家長更愿意談“治愈率”,他們還能舉出很多真名實姓的“矯正成功”例子。
何謂“治愈”或“矯正成功”?答案很簡單:孩子變得聽話了。恰如文清的父親當晚發給她的那條長長的消息,在表達歉意的同時,也不忘提及“希望你好好聽話”。
把孩子當作“問題”來看待的家長
直面孩子的問題,而不是把孩子本身當作“問題”來看待——這些家長對此顯然沒有足夠認識。
然而,所謂的“矯正”往往并不成功。
從新長征出來后,學員與家長的關系并沒有得到改善。陳靜決定與父親“老死不相往來”;趙小帥對父親“拳打腳踢,用臟話罵他”;2000年出生的文清如今一個人從老家黃岡到武漢做生意,有時候半夜起來處理文件,她總在想,絕大多數同齡人尚在父母的呵護下讀書,而初三就被送入新長征的自己卻獨自經歷了那么多……
就在文清的父親發給她那條長長的致歉消息時,她的母親給她打了一筆錢。“我媽讓我不要資金都放在開店上,用完了就說,要買什么就買。”這已經是文清眼中,母親的溫暖表達。
他們羨慕那些看起來單純快樂的同齡人,“家庭條件中等的,父母關系很健康,孩子從小被呵護得特別好”。
那種感覺,就像一個沒有零食吃的孩子,看見小伙伴樂滋滋地含著棒棒糖。
應采訪對象要求,韓笑雪、藍琪、陳靜、文清、趙小帥系化名
本文來源:解放日報·上觀新聞
作者:向凱
- 上一篇:近3萬噸洋垃圾偽裝入境被查 有害廢料仍發煙發熱[ 04-10 ]
- 下一篇:男子被控毆打4名兒童受審:小孩太吵影響妻子養病[ 04-11 ]













